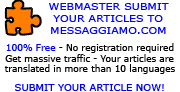在其他人苦難的一個便宜的假日(跟上mordechai vanunu在以色列)
我的一喜愛的乐章是性手槍的經典『假日在阳光下』 -從線開始的歌曲, 『在其他人民的苦難的一個便宜的假日』。 這在以色列將做我的假日的一段貼合墓誌銘,除了$3000飞机票意味它不正確地是便宜的。 我充分去以色列憂慮。 知道什麼我們全部知道垂懸在那土地是使任何人惶惑的足够偏執狂和痛苦的背景,但是我也去運載一個秘密-那我是Mordechai Vanunu的朋友的,并且我是緊張的關於我會得到的反應如果這真相突然变得公開。 我的朋友Morde完成做的某事18年监禁多数人民在這個國家认为英勇。 Morde告诉關於在一家地下工廠被开发在Neqev沙漠的一個秘密藏匿處的世界WMD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认识的多数人民認為他做了世界極大的厚待,但是他自己的國家願望的Morde多数人民保持他的嘴被關閉。 的确,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他奸賊! 為了设法瞭解对于我的朋友的這個态度,我设法談與關於他們的態度的地方人與核武器。 我收到的答复是驚心的! 「他們在只那裡,我們的最後一招」一位表達清晰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對我說。 「在案件我們完全地得到超出量」。 「好…什麼然後發生?」 我要求。 「好」,他說, 「然後我們毀壞大家!」 悲劇地,這不是一個例外。 幾乎,在我征求了從出租車司機、咖啡館工作者或者旅舍職員的一個觀點關於以色列的核能力時候,詞『末日審判』將出来。 并且這些辨護者似乎為了觸擊這果斷吹動反對他們的鄰居,他們也許的確需要採取行星其余與他們的相當的接受事實! 沒有每個以色列人感激地接受了這职位。 的确, 『自由Vanunu』競選有活躍和平運動家一個強的地方分遣隊。 這些地方活動家是我遇見在我的逗留期間在以色列的某些最印象深刻的人民。 在澳洲他們將是印象深刻-主要年輕,理想主義的大学生,有對世界和平和全球性裁軍的一個承諾的-印象深刻,但是不非凡的在我們的上下文。 在雖則這上下文,长大在環境裡,因此投上陰影由暴力和恐懼,這些勇敢的年輕靈魂引人注意了像光亮的光。 以色列文化的猛烈邊比它在Morde的發行的那天未曾是有形對我。 我旅行了與我的在天的朋友將團聚的許多數以萬計英里他任意走了。 在我的夢想我想像我們的團聚不計其數的时间。 Morde通过與他的財產的那些門將走在一隻手,并且我和一些個朋友和家庭在那裡擁抱他和帶領他。 我真正地沒體會,直到我到達了監獄從現實那個場面的我虛構的描述多遠將证明是。 有数百我們在監獄,并且大多数不是Morde的朋友。 当他的發行的时期临近,我设法移動朝我總是想像自己站立的監獄門,当Morde走出去了。 我很快找到自己被緊壓入一個惱怒的暴民的中部。 它一定是其中一我的生活的最討厭的經驗。 人整體大量似乎起泡沫以侵略,并且單獨的其中每一競爭抓他的方式到前面,為了什麼確切的目的不是完全地清楚的。 我不可能感激地瞭解唱歌總共『這裡的聖歌我們是,這裡我們去,這裡我們去』,但是我以后被告诉了『死亡』和『奸賊的』詞對被歌頌那天的所有佛經是中央的。 在反射我現在認為它是的一件好事,當Morde通过警察一起包裝了我們那么緊緊的那些監獄門的時候來了我沒有能移動肢體。 什麼防止了我擁抱的用尽Morde也防止了我的鄰居到達他有更加陰險的意向的。 與我的朋友的汽車它的比一個消弱的盤區和雞蛋陣雨感激地离开了沒有更多。 一個反對者设法及时捉住汽車登上他的摩托車,但是在關上入車的邊以後他丟失了他的登上,并且『自由的人』能進行在和平。 在監獄事然後开始解開。 充满未解決他們的憤怒,暴民开始发泄他們的在其他目標的侵略。 我在这中找到自己被清掃像打破在我的頭的波浪。 一秒钟我走往我的公共汽車。 下片刻我由一名惱怒的猶太教教士帶領的暴民圍攏,尖叫在他的聲音頂部。 『回家』我可能瞭解的唯一的詞組。 平等地毫不含糊的雖則是在我的身體、解雇登陸在我的腿和唾沫被安置在我的面孔積累的概略的手。 在這種情況下我沒看見逃命任何道路,因此我在禱告的位置一起安置了我的手并且低下了我的头,研究的至此成功的戰略,如果您拒绝还击,人通常非常勉強痛打您。 它运作。 一個人劫掠了我从后面用兩隻手并且拖拉了我在暴民外面的中心。 我做了它回到我的公共汽車,不用进一步事件。 所有此將是水鴨子的有Morde和I然後能上飞机和飛行回到澳洲。 不幸地當局裁决這個『自由的』人不應該允许离开國家,亦不任何地方在邊界或外國使館附近去,亦不有與『外國人的』所有聯絡。 『外國人』制約瞄準了外國新聞社。 即使如此,技術上,我不允许花费與我的老朋友的廣泛的时间不冒險看見他再拘捕了! 在那同樣天他的發行的晚上,我們簡單地團聚了。 不幸地我非常哭泣我真正地沒得到機會告訴他全部事我为那片刻做准备。 我可以暫時希望的所有是一天我們將適當地追上或許-在一些啤酒這裡在Oz土地。 我知道Morde將想要那。 使Morde脱离以色列的確是Vanunu競選的下大挑战。 我不知道多么堅硬這將证明是。 我知道我有血淋淋的困难时期出去我自己。 在我的情况不是他們沒有想要我(他們舉行了飛機的離開,直到我在船上得到了)。 他們似乎堅定告诉我他們沒有想要我。 我由威逼戰術的其他和平活動家機場職員使用的警告了。 諷刺地,我通过所有四個安全檢查站最初做了它,不用被停止。 它是,只有因为我進行了最後的門衣服的一個年轻人跟上了我并且說, 「劳驾先生,但是能我看到您的護照」。 他然後告訴了我有『問題』,并且他會需要保留我的護照,直到解決了『問題』。 我然後被拖曳了入一間小屋子開始審訊,身體搜尋和行李考試的三小時過程。 在最后定案是我自由去,并且沒什麼關於我的袋子內容的嫌疑犯,但是袋子是嫌疑的,并且他們都不可能在船上被採取当手提行李。 这意味着我可能運載與我我的照相機,但是不在我的照相機盒,我的膝上型計算機,但是沒有我的膝上型計算機盒,我的摄象机,但是與肩带的不是袋子我用力拖了它,我的牙刷和漿糊,但是沒有我的化妝品請求和甚而我的棕櫚飛行員便攜式的鍵盤,但是不是少許乙烯基塵土夾克我保留了它。 我可能採取什麼我喜歡,只要我運載了它在我的胳膊。 它是比賽,雖然他們设法保留在整體考驗中的不显现表情的脸。 我我的部分拒绝在船上得到,不用大多数我隨身攜帶的項目。 在最后他們同意給我一個大纸板箱投入他們。 并且我在其他人民的苦難的便宜的假日如此結束了。 但是实际工作現在開始。 对于我回来了在家,但是我在耶路撒冷把我的在聖喬治的大教堂裡面區域的朋友留在,好主教提供了他聖所。 Morde不可能留下大教堂地面。 他有每出口的至少二位記者,採取轉移报道他的每天的運動24小時。 如果走出去的Morde嘗試入街道,他將被圍攏并且立刻被辨認,并且被給算作是它问题的自豪感负责对他的死亡本機的数量, Morde的生活公开以上几分钟大概不會持續。 我希望在澳洲看我的朋友後面這裡。 我想知道澳大利亞政府是否有勇氣提供他公民身份?DBS. 2004年4月
『戰鬥的』父親戴維・史密斯-教区教士,社區工作者,專業戰鬥機,在1986年父親三-会见的Vaunu在悉尼。 他們是朋友自那以后。
Vanunu在父親戴維的書以为特色, 『性、圓環&聖餐』。 当您為戴維的時事通訊簽字在www.fatherdave.org时,得到一個自由預覽拷貝
文章來源: Messaggiam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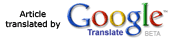
Related:
» Run Your Car On Water» Recession Relief
» Advanced Automated Forex Trading
» Profit Lance
網管得到HTML代碼
加上這條到你的網站!
網站管理員提交你的文章
無須登記!填寫好的表格和你的文章是在 Messaggiamo.Com 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