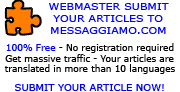束缚的领带
我不知道它怎么开始了或谁发射了它。 然而在所有的几年我家的妇女以后死了(他们是所有的创始者我们的主要家庭事件和thingamajigs)。 在困境这些妇女我们的家庭整体留给主要由人组成)之后。 近年来,我开始注意我听见长大和不断地今天收到关于的评论我们的家庭怎样从彼此是相当地不相似或极大地遥远的,并且我们怎样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来信从那其他家庭明显被对比了。 作为一个年轻成人,我卖了入那不一致,并且我最终开始相信它。 现在,我慷慨激昂地从顶向下想要知道这错觉怎么产生了。 如果这个“假定”拿着水,我必须为我自己看。
多年来,我们从未甚而击了眼睛,当某人描述了我们的氏族作为是“遥远地不同的”或,因为我们“居住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很少参观甚至与互相谈了话更多的一个一致的依据。 (一些住在芝加哥之内的不同的城市或从伊利诺伊一共移动了)。 因此行动或缺乏由一些辩解与评论“好您知道我们怎么是”。 只在最近把I开始令人恼怒再寄,每当我听见了那个评论。
我常常地,当一个可信的答复不是足够振振有词遏制我好奇的难满足的胃口,我允许我的头脑远航入一个客观方式。 结果,我从”智力上去除自己认可观点的我的亲属的我习惯的“家庭字符与一个没有偏见的角度。
必须细听这误解年和年,今天我最后是富挑战性我自己尝试和改变它。 我想要最后创下纪录平直。 我希望,在一些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不会必须再听见它,因为它不会被说出。 至少不在我的听力范围。
我从旅行回到我长大的有风城市芝加哥。 在我的与我家的参观期间,我的眼睛对许多现有的修改被张开了,虽然一些是新的给我。 我说充满回响的自豪感,变动我目击了伤心。
首要,二我的表兄弟最近与非常支持并且爱他们的惊人的妇女结婚。 两个有亲爱的孩子在短小保留我的表兄弟和他的一个妻子没什么在他们的脚趾的五岁以下。
只昨天似乎我姐妹,表兄弟和我是到处乱跑在家庭在一起期间的那个。 我们是注意的核心和所有我们的伯父; 伯母和资深表兄弟在美国溺爱。 此刻我们是换了地方与那些长辈的那个(一些去世了,当其他很好入退休年并且/或者在不健康)时,并且我们在我们的子孙和孙现在溺爱。 等级这新潮的交换即刻地要求我开始应付我自己的死亡率。 这些情景不断地被再声明在我的灵魂里面,并且我更加被提醒时间等待没人。
只有我的甥女(引人入胜的好漂亮的东西或人她是,过去常常坚持我象胶浆后面在天,并且总是要对跟我学到处)现在有她自己的一个起泡的女儿! 因为它似乎发生了在夜,我仍然开始应付那一个。
它是反射性的看我的表兄弟(谁可以被描述当眼睛糖果并且一样优良是象Denzel华盛顿的和在一个酥脆包裹熟练地包裹的Shamaar Moore的全部,并且有深刻的笑涡,如我的姐妹有。 他是他自己的报纸编辑。 他坐了并且协调与我们的亲戚,并且表达清晰谈论用缜密术语“增长的伙计”与em最好谈话。 (我肯定他将喜爱读我写道我曾经换他的尿布!)。
当我注视入我的甥女和这个特殊表兄弟时的面孔,我仍然构想他们,他们在婴儿时期。 由于我设法不观看他们以那方式,我是无能为力的。 它是,好象我爱恋注视入我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的面孔,当我首先带来了他们家庭从医院。
另一个表兄弟写着一本书(没有我不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家的唯一的作家!!)。 他和我亲密无间,当我们是十几岁,并且我们总是进入淘气。 虽然,当我们被捉住了,他是能维护一张不显现表情的脸的人(因此今天适用)的同样,因为我没有同样多克制象他,我总是会破裂入泪水沾湿的笑声和终于导致需要我们的大错的秋天。
他和我享受关于一个老,老笑话的衷心催人泪下的笑。 我们分享的熟悉的vibe,当少年仍然保持一样舒适和知交象一双老袜子。 我最后有机会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最后遇见他的妻子。 他有是一个的家庭感到骄傲。 他为他自己很好做了,并且我为他感到骄傲。
另外表兄弟有他自己的发声公司。 他做“声音”在普遍的录音艺术家音乐会,并且很多他的顾客是我们在录影和收音机看见并且听见的那个。 我有机会与他的女儿(谁充分坐和谈话以很久以前过世)的我的一个喜爱的伯母命名。 她促进她的教育并且是在她的途中对成功。 充满自豪感的工字金属梁,当我听见我家的青年人有的进步。
由于我在我的生活中创造的地理距离不要家庭栓,因为我知道它那时将是同样与我的表兄弟和我的甥女。 人们长大,生育并且开始建立生活那相互依赖的生活他们体验了与他们的直系亲属。 但是转折的这些类型不应该发生? 由于“现代性”在和我家树,我与新的位置一起认可了它新趋向它在体会投入我它不是更坏的,亦不更好,它是公正不同的。 嘿是什么是,并且生活去在。
一些年迈的和已存在的变动从肉眼不立刻是可认识的。 可能它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变动,但是总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的一个事实。 必要的所有任何人做看它明显地是采取一只视觉上详细的雄鹅,并且那里它在全视图。 什么的现实我看了关于整体上我家是妇女以及人总是维护了平稳的就业。 我不谈论5年这里, 3年那里。 我谈固定的种类的就业。 您知道类型。 是在非常同一个工作30正年的那个。 那些伙计。 我知道您也是有一些那些在您的家庭。 多数家庭。 这些人度过了被延长的岁月在一个工作。 今天他们从他们的就业场所在和谐和歇息中退休了和居住他们的生活剩下的时间。 这是什么人们自然地做,在不再能做之后什么他们习惯了做他们的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部分的。 其他放弃了一个工作并且承担了别的。 上帝保佑em。 当我从一个工作好了退休我的!!!!!! 每天我设法保证我的退休将是那。 退休!
因此说,我不看我家“怎么不同”。 在哪里真实的官能不良? 因为所有家庭陈列某一类在本身之内的有气质行为我说“真实”。 每个家庭有他们去,无需看见或讲话的时间流逝,特别是如果距离是因素。 每个家庭有他们不喜欢也不喜欢一样的成员。 那里总是突变、行为或者在鼓动一些的亲戚之中的个性区别或者特征。 问题的事实是我们不会喜欢所有我们的亲戚。 永远将有一,二或者可能几厌烦哎呀在我们外面的我们的家族,不管他们做或不做。 我肯定我驾驶其他到燃烧边缘与气质的我有所有我的生活!! 那些是事实现实有家庭。 然而我们不沉溺或忽略他们并且做物质问题的它。 我们容忍这些区别或较小心烦,因为我们是家庭,并且我们全部被栓。 严紧的重要性我们所有份额应该胜过无意义刺激剂。 最终结果是最什么事态之间的区别,并且什么事态。
真正地受到我的注意的最统治的美德是我们都不是吸毒者。 我们都未在监狱,也没有犯罪纪录。 男人或妇女都不是完全虐待对或滥用由他们重要他人。 没有一我家成员甚而抽香烟,没有一!!! 在一个困厄的世界例如我们今天居住,前特征是重大的并且说关于人,更加重要地一个整个家庭的可怕的全部。 因为我们居住我们的生活作为社会的有生产力的成员我们是否是显著地不同的? 把我难住。
我承认我们在是上有一阵子是所有有罪的遥远的。 当大多数妇女开始的滴下象死的飞行没人会再表现作为“家庭”我推测。 多年来我们在毁灭保持。 我们在那上是有罪的。 因此起诉我们。
判刑我们,如果您将,因为多年来每名妇女(谁是通常保留团聚加上在老练的家庭)的胶浆从某一排序癌症得到了病和最终死缓慢,痛苦的死亡。 所以,留下人做什么去世的那些妇女做了最好。 被留下的人没有兴趣在告诉亲戚计划感恩晚餐、生日聚会或者周末滚刀瘤。 他们没有必须。 他们漫步到女朋友房子,或者邻居安置或您的地方吃饭的客人并且劫掠了膳食。 什么我设法说是,它是妇女,至少我家后面的在天,谱写音乐一切。 不再他们在我们之中,人困惑不解。
当现有的妇女长大并且结了婚,我们趋向了给我们新的家庭的妇女。 它was/is一个自然进步或它如此似乎。 我们接受了计划者和orchestraters的职位。 我们是打那些电话并且邀请我们的伙伴的亲戚到我们的感恩和圣诞节晚餐的家等等的那个。 我猜测,一旦我们去世,如果没有妇女整理我们停止的地方,然后这曩年将重复自己。
要记住的观点这里是我有是我的家庭成员的亲戚。 我要求他们与所有他们的怪癖、特异、突变、弱点和跌荡的行为。 我们全部有他们,并且没人是完善的。 我们全部从布料同样螺纹被编织。 他们是谁的一部分我是今天。 他们是不显眼地移动在我的静脉中推生活入我的血液。 他们是我的根和我的结束和我的起点。 他们是我的共鸣板和我的坐垫。
我必须旅行回到有风城市芝加哥,并且我认为我回去拜访一个不适的伯父,并且建立一再联接的一些外表与距离和时间拉扯我的那些和我的是高兴的我旅行了。
我意识到我有任何人神智清醒会是幸运的承认和认可作为是他们的家庭的一个家庭。 我有是一部分的我是编辑,音乐家, soundmen和作家的人。 改正我,如果我是错误,但是不要是我们看见的这些某些同样职称信用什么时候滚动在电影的结尾? 不多数吵闹声他们的度过大量的时间的脑子学习成为,当出席常春藤同盟时在美国教育的这些某些是否是位置? 并且这里我在足够幸运有这样的成员在我自己的家庭之内。 肯定我们也许看或每天不互相讲话。 但是我保证您,如果我需要他们我意味真正地需要他们,他们毫不迟疑地在那里为我。 我可以现在说那,但是信任我我总是没有感觉这样。
当我结婚了我天真相信我不再需要我的生物家庭。 (我怀有我的妈妈的怨气,因为她告诉了我,当我是一个女孩我的生物爸爸是死的。 很多我家知道真相,并且,因为没人告诉我中的任一不同我是恼怒与大家,当我发现了在这“爸爸事务之后的”真正的成交。 几年后,和与深刻心伤和失望,我发现了不仅是活我的爸爸,但是在最近十年之内,他从谋杀的他看见妇女的丈夫监狱释放了他推测什么时候约会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不要我们联合他,并且所以她告诉了我们他是死的。 我必须承认这是这一次我抱歉我总是很好奇的。 至今,我甚而不知道我的父亲的名字亦不我要。 幸运地,我的妈妈和爸爸未曾结婚,因此我可以感激地说他不作为我美妙的家庭整体的部分)。 我在我的创伤和泪花埋没了我的”自然家庭"。 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体验了足够的创伤和痛苦? 我认为。
我由于坏判令责备了我的整个家庭在我的母亲部分。 他们全都想法我认识我的爸爸活,至少。 当那新闻在我,被放置了想象我的毁灭!! Whew!!!!!!!!! 但是真实对形式,我最终回弹。 许多家庭戏曲有很多,但是矿死亡和精神创伤有很多。 难怪我们使吃惊。 需要我们的几年能在那么快疏松许多妇女以后恢复。 我们需要一分钟重新组合,重新聚焦,并且发明另一项比赛计划您是否不会说? 什么家庭不会? ? 但是我们所有设法生存。 我来自幸存者的一个整个世代。
我唤醒的电话来了,当我离婚了,并且家庭我认为总是在那里为我不终于是。 最终我从他们慢慢地被放逐了。 以后那发生了我没有感觉,好象我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地方”。 我没有感到我属于“家庭”单位。
如果您结婚,并且您认为您结婚的家庭在那里为您,得到离婚。 经过重新考虑为趣味去和请得到分离。 没有其他方式提醒血液,虽然经常怀疑,比水总是厚实的一。 如果您如此渴望,我鼓励您对电子邮件我并且告诉我最终结果。
是的点是我被画了回到我不幸地设法否认和忽略的非常同一个生物家庭。 它去表示您,我们总是被画回到我们支持某事。 它是我们不可能否认的必然性。 我知道我不可能和不再想要否认我的。 感谢那里上帝是每天学会的教训。 我在哪里没有我家? ? ?
今天,这位作家不关心它怎么开始了或谁发射了它。 没关系“dysfunctionally不相似的”人民怎么认为我们是,假如是亲戚或某人外部的。 我们是同一个基因的所有部分并且互相爱。 可能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方式显示它。 可能我们不陈列我们的爱根据社会怎样口授我们应该。 但是底线是我们全部连接作为一个,无论一些与它战斗,掩藏它,跑远离它,否认它,掩盖它,忽略它或否认它。 我们是家庭。 就我所关心,我家是伟大大成交。 我家是我不介意被栓到为这些是我的领带束缚的这一困境。
ÃÆ'â⠂¬Å ¡ Âà ‚由C. v.哈里斯的© 2005年。 版权所有。
真实的故事回到有风城市芝加哥的一次womans参观怎么提示她观看她的家庭方式他们“”真正地意识到她的家庭包括真实的幸存者。
文章来源: Messaggiam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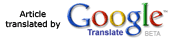
Related:
» Home Made Power Plant» Singorama
» Criminal Check
» Home Made Energy
网管得到HTML代码
加上这条到你的网站!
网站管理员提交你的文章
无须登记!填写好的表格和你的文章是在 Messaggiamo.Com 目录!